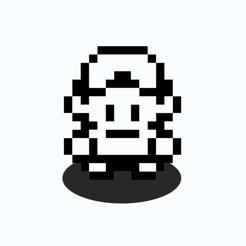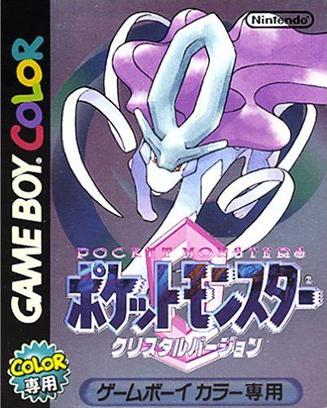5. Xbox、Switch
R:其实我们在上一期曾稍稍触及电子游戏机这个话题,因它们已成了我们居家生活的一部分(J:又抽到我写的题目!难道是天意LOL)。说来也是有趣,我们竟是在将近三十岁的时候才开始体验游戏主机;在人们通常的印象里,只有十几岁的小孩子(也许还有在校大学生)才会热衷游戏。
和许多同龄人一样,我们从小学开始,也曾玩过不少电子游戏。就我自己而言,小学三年级时家里有了台式电脑,自此开始陆续在电脑上玩过《红色警戒》《帝国时代》《星际争霸》《魔兽争霸》等即时战略(RTS)游戏;《反恐精英》等射击(FPS)游戏;《极品飞车》《科林麦克雷拉力赛》《暴力摩托》等竞速游戏;《仙剑奇侠传》《暗黑破坏神》等角色扮演游戏(RPG),再加上大学本科时很火的《三国杀》和《遗迹保卫》(DotA),读博后玩上的《文明VI》。此外,在文曲星(电子辞典)上玩过《英雄坛说》,在手机/iPad上(一度非常疯狂地)玩过《万智牌》《神庙逃亡》(Temple Run)《保卫萝卜》《Cytus》《猎鹿人》(Deer Hunter)《虚拟乒乓》《刀塔传奇》《猫咪收集》(猫集め)《谜室》(The Room)《真实赛车3》(Real Racing 3)《三国群英传霸王之业》《密境对决》《七大奇迹》(Seven Wonders)《瘟疫公司》(Plague Inc)。
虽说这也是串长长的列表(有待你来补充),但玩这些游戏所使用的设备(电脑、电子词典、手机、平板)都不是仅仅为玩游戏设计的。游戏是它们的功能之一,但买这些设备的理由,至少名义上从来都不仅仅是要玩游戏。买一个机器仅仅用来玩游戏,这个观念在九十年代的思维里是比较难接受的;有个说法叫“玩物丧志”,表明玩游戏与那种努力学习/工作的道德是相互矛盾的。这背后的理由,不能仅仅归结为建国以来汉语话语中那种“艰苦奋斗”、“吃得苦中苦方为人上人”的禁欲主义(asceticism);它同时也是基于游戏这种活动本身的性质。许多人比较习惯于工具理性(instrumental reason),追求功效和实用;在他们看来,一项活动必须是为了…而做,换言之,必须有自身之外的目的。而游戏恰恰不满足这个标准:游戏是它自身的目的,我们玩就是为了玩,不为别的什么。如若玩游戏是为了别的什么(赌博、打比赛、拉关系),它就变味了,不“好玩”了。于是,从一个局外人的角度看来,玩游戏的人在游戏世界里追求的东西都是毫无意义的。你练了一个99级一身神装的账号,游戏一停服,什么都没有了。我们因此会觉得游戏浪费时间。
由此看来,像Xbox、Switch这样的游戏主机,简直是专门做出来浪费时间的。它们其实也发展了许多代,比如任天堂许多年前出过Game Boy、GBA、GBC,而我那时只能在电脑(这个不只是用来玩游戏的设备)上装一个GBA模拟器玩《神奇宝贝》——换言之,即便人格已经独立,仍然是偷偷摸摸,不敢“大逆不道”。去年夏天,完全是借着疫情隔离在家的契机购入了Xbox,即便这样也还是经历了好一阵的犹豫:会不会“玩物丧志”?不过,这种遮遮掩掩的羞赧,似乎也成了游戏乐趣的一部分:玩游戏总感觉是在“偷玩”游戏,却正因为是“偷玩”而格外好玩。
如今,开玩Xbox已经快十个月,开玩Switch也三个多月了,终于能以比较平静和自我宽宥的姿态来思索电子游戏这种兴起不过几十年、却彻底改变了人类想象力之版图的事物。一项活动的目的在它自身之中,这本没有什么不妥;我们不妨说,艺术对于艺术家是如此,旅行对于旅行家是如此,工作对于工作狂也是如此,就连挣钱,都可以是为挣钱而挣钱。关键只在于,这个过程本身是否值得经历。
放下有关目的、效用的执着,我倒想赞叹一下如今电子游戏的发展已经使我们完全有可能创造并欣赏无数在现实世界之外的虚拟世界。我在Xbox上最喜欢玩的两个游戏,《极限竞速:地平线4》(Forza Horizon 4)和《刺客信条:奥德赛》(Assassin’s Creed: Odyssey),都是所谓“开放世界”游戏。《地平线》系列一改以往赛车游戏“一切围绕比赛”的设定,将驾驶本身变成了一件具有节庆意味的事情。在意大利和南法的乡间,在澳大利亚的沙漠和雨林,在爱丁堡城堡脚下青石铺就的街道,你仿佛一个自驾的观光客,只是顺便去参加几场比赛。除了比赛,你还可以探索雪山之巅、秋林深处、车辙纵横的泥潭、人迹罕至的溶洞。你可以完全把它当作一个摄影游戏来玩,也可以在拍卖行里投机倒把,赚得盆满钵满。而《奥德赛》,这个“大型旅游模拟器”,更是直接把你带回伯罗奔尼撒战争期间的希腊,让你在满天繁星的海上伴着船歌掌舵航行,在阿卡迪亚的山谷间打马疾驰,在雅典卫城的峭壁上徒手攀岩,在克里特岛的炎炎烈日下寻找史前文明的遗迹,在科林斯的市场上讨价还价,甚至偶尔去盗个墓。作为一个学哲学的人,我做梦都没想到会见到栩栩如生的毕达哥拉斯、恩培多克勒、希波克拉底、阿那克萨戈拉、德谟克利特、苏格拉底和(童年的)柏拉图。(历史控还会因为莱奥尼达斯、薛西斯、希罗多德、伯里克利、阿斯帕西娅、克利翁、斐迪亚斯、索福克勒斯、欧里庇得斯、阿里斯托芬、德谟斯提尼、阿尔基比亚德、泡珊尼亚斯、布拉西达斯等人的“复活”而兴奋不已。)当苏格拉底抄着自制的三叉戟来劫狱的时候,那种历史的触手可及感是永远无法通过阅读文字达成的。

有了这无限丰富、容许无限可能的虚拟世界,我们随之也有了各种看待和研究游戏的角度。游戏人类学、游戏的技术哲学和政治哲学、游戏神学,似乎都大有可为。之前看到过一篇《开放世界的创世神学》,而我几年前也写过一篇《手游政治哲学》。
J:关于电子游戏,我的经历跟你还挺不同的,不知道是否主要是由于性别(gender)差异。记得上小学时,我有一项周末娱乐活动就是去同学家玩电脑。虽说是去玩电脑,但其实是几个小伙伴围坐在电脑前看一个人操作,玩的游戏有《红色警戒》、《反恐精英》和《星际争霸》。也不知为什么,我是在场唯一的女生。我自己对这类打打杀杀的游戏没有太大兴趣,几乎没有碰过鼠标和键盘,印象最深的是尤里这个人物,还有个大鲨鱼一样可以空投导弹的苏联飞艇……(R:基洛夫空艇……)我还围观过我表弟玩《太阁立志传》,我堂弟玩什么已经记不清了。去女性好友家也会有玩电脑这项活动,比如《大富翁》、《美少女梦工厂》、《帝国时代》。小学有个机房,那时电脑还是DOS系统,有一次我输代码误打误撞,竟然打开了(不知道是不是老师装的)《仙剑奇侠传》第一代,但才刚到赵灵儿出场,就下课了。

大概是小升初的那个暑假,不知道我妈妈从哪儿弄来几张盗版游戏碟片,让我一个人在家没事时可以玩玩电脑(我妈就是这么的酷炫)。但是,因为我们家电脑的配置不够,而且盗版游戏运行起来很卡,我唯一坚持玩了一阵子的就是《仙剑奇侠传二》了。然而作为一个资深路盲,走迷宫对我实在是太大的考验:我当时玩到了一个卷轴里的“化境”,因为不认路,找不到大boss,便总要打无穷无尽的画妖,最终就放弃了。
到了初中,班上风靡过一阵《梦幻西游》这个网游。说来好笑,我的人物角色还是一男性好友帮我建的,取名“梦魂月”(听起来着实不像我的风格),等级也不是我练的,我只是偶尔登录看看风景。也有别的朋友邀请,一起玩过其他类型的游戏(比如《冒险岛》),但也都浅尝辄止。我的操作着实糟糕,至今打《超级马里奥》这类游戏不会跳跃,开赛车不会转弯,对战时不懂走位和退避,玩啥都有一种横冲直撞的送死倾向。加之打怪练级对我实在是一种耗时费力的“劳作”,而我基本上是个“现充”(「リア充」,指没有ACG生活就很充实),对游戏向来不大有耐心。硬算的话,我可能还玩过“人人网”上背单词和偷菜,还有QQ上的什么小游戏?(R:抢车位、好友买卖?)
后来我再接触游戏的契机,其一是我们拥有了iPhone、iPad这类移动设备,而手游也日渐多了起来;其二便是受你影响吧——你拉着我打过不少局《三国杀》、《万智牌》、《秘境对决》这些卡牌游戏。这些年来,我自己玩过的游戏有经营类的《卡通农场》(Hay Day),著名的《阴阳师》(手气太好,刚玩就抽到三个最厉害的SSR,于是“肝”了好久),被你叫做“捡垃圾游戏”的《边境之旅》,可以建造迪士尼乐园的Disney Magic Kingdoms,玩法像下棋但剧情无聊的《权力的游戏》,好多换汤不换药的“消消乐” (以Candy Crush最为著名),还一度因为玩不了Pokemon Go而玩了一个山寨国产版。疫情以来,我们在Xbox上一起通关了《分手厨房2》(本名Overcooked, “煮糊了”),我还继续发扬光荣的围观传统,看你打了好久的《文明六》和《刺客信条:奥德赛》。最近三个月,我爱上了iOS版《动物森友会》,玩法简单,小动物可爱,对我还有点类似沙盘游戏的治愈效果。
不知道有多少女性玩家像我这样,对传统“枪球车”游戏非常无感,只想在游戏里心情愉快地追求Love & Peace,但又不喜欢visual novel或者和虚拟人物谈恋爱。想来游戏的开发商也是蛮厉害的,在我这类人群这里竟也能开辟出相当可观的市场:我虽然害怕game变labor,但不知不觉也贡献了好多时间和精力,以及金钱。

不能否认的是,人类永远需要闲暇,需要游戏(参见Homo Ludens,《游戏的人》),但从我有限的经验而言,如今的掌机手游和从前的电脑游戏似乎还是非常不同的。我小学去小伙伴家里围观玩电脑也好,高中班上男生组团逃课去网吧打DotA也好,玩电脑游戏更多是一种社交方式,是一种构建小团体身份认同的手段。我小时候也体验过游戏主机上的《魂斗罗》、《坦克大战》,感觉它们也更多是为了“合家欢”的场合准备的。进入手游、高性能主机时代以来,游戏的画面变得更为精美了,内容的丰富度也得到了大大的提升,但是玩游戏似乎变成了一件孤独的事情?
R:还真是这样。网速捉急的时代,游戏公司尚且千方百计地要求玩家在线游戏(主要是怕玩家作弊;通过在线的设定减少了作弊,再提供充钱氪金“作弊”的渠道以牟利),如今主机端上想要在线多人却还得额外订阅一项服务(Xbox Live Gold;Nintendo Switch Online),不订阅就只能打单机。
人类开始有组织、有规律地玩游戏之初,所有游戏都是多人游戏,是你所说的“社交方式”。维特根斯坦在《哲学研究》里甚至提出我们的语言本身就是一套游戏,语法是这游戏的规则。在这种模式里,游戏世界本身有多么仿真、画面和音乐有多么精美,其实是次要的;彼此更重要的是通过共同参与游戏活动而实现或合作、或竞争的共鸣呼应关系。一起玩一个游戏,即是进入同一种节奏。直到我们上一代人,游戏的用具仍然是非常符号化的,如象棋围棋、扑克牌、麻将等,而且游戏者的身体往往是同时在场的,就如同我们一起玩《分手厨房2》时一样。这种游戏不会需要很高的分辨率和很快的处理器。反观如今这种“孤独”的游戏体验,它就如同语言不再是用来实现谈话,而成了诗歌一类的艺术品,语词本身而非它的社交功能成了关注的焦点。游戏的焦点转向了精细、仿真、代入感;玩游戏的体验如同孤独的个体坐在剧场中、与一个由表象构成的“世界”而非活生生的他人打交道的体验。(丹尼尔·丹尼特所谓“笛卡尔剧场”。)在这样的游戏世界里,玩家即便有机会遇到其他玩家,他们多半也互不相识,不会有游戏之外的联系,于是社交仍然让位于“游戏体验”本身。
我一度关注过游戏世界里这种自发生长、组织的社会遵循什么样的规律。乍看起来,游戏似乎为各种有关“自然状态”与社会契约的政治理论提供了大片的“试验田”:它提供了一个将历史和法律悬搁起来的公共场域。然而,我却渐渐发现,游戏开发商如何设定其世界、要求玩家取得怎样的成就、容许玩家以怎样的方式互动,对玩家之间最终形成的社交模式有巨大的影响。这个社会不是从零开始生长;恶的种子往往在游戏本身的设定里就种下了,正如“电车难题”(the trolley problem)这种思想实验的恶在实验的设计本身之中就种下了。我发现,游戏(这里专指网游和多人在线的手游)的世界是一个一言堂(totalitarian)的世界,管理员(administration)凌驾于这个世界的种种社会规则之上,构成了这个世界最基本的不平等,并通过创造各种适用“丛林法则”的情境来加剧不平等,让玩家自相残杀以巩固自身的地位。这无疑是有关我们所生活的“现实”世界的一个既惊人、又恰切的隐喻。
J:既然影视作品能被视为文学的延伸,游戏何尝不是电影的延伸(君不见,多少东亚系放弃了文学研究传统,转而搞起了影像和传媒研究)。优秀的文学作品、电影和游戏的确有相通之处,比如当年CGI技术的集大成者《最终幻想》系列,我没有真正玩过,但是游戏的画面和配乐让人非常难忘;而现在的《奥德赛》和《大革命》,我虽然不喜欢里面血腥暴力的打斗场面,但还是被华美细腻的场景和相当有历史感的叙事所吸引,所以一口气读完了貌似是游戏脚本的小说。如果我来操作手柄,我要么去巴黎圣母院的塔尖看看风景,要么去雅典找伯里克利的老婆做向导,来个神庙一日游——感谢游戏贴心地为我这样的玩家准备了纯游览模式。前年大英博物馆来蒙城举办木乃伊展,其中以第一人称视角探索金字塔和制作木乃伊的高仿真动画,说不定用的就是Ubisoft做《刺客信条》的技术。



不过,同为开放世界游戏、画面也足够精美的《荒野大镖客》和《侠盗猎车手》就不吸引我,因为我实在不向往那种在“利维坦”设定里,只能靠打砸抢维系的悍匪生活。而另一个极端则是那种“创世”类游戏,比如《我的世界》(Minecraft)(可能《动物森友会》Switch版也是,但没有那么硬核):初始世界需要从像素如此之低的一砖一瓦开始建造,这难道是在对我实施降维惩罚?
随着游戏技术的提升,玩家貌似拥有越来越高的自由度,然而设计游戏规则的算法才是这个世界的“神”,玩家如何感知游戏世界、如何行动、如何感知其他玩家、与他们交流互动,这些都是可以预设的。你说这类似政治哲学的思想实验,我倒觉得社会心理学可以开拓一下这个领域,免得再有被试在现实生活中被电击或者当成囚犯。
R:开放世界做得过头了,做到毫无剧情引导的程度,就成了一个接近真实世界的世界。这个时候,有关“玩游戏有什么用”的问题就会卷土重来:既然真实人生已经如此艰难,为何还要“虚拟人生”?当然,玩家可以有一千种理由。有一类人精力格外旺盛,只过一份人生似乎远远不够。游戏以虚拟现实(VR)的方式挑战着人生固有的有限性;它希望人有机会追逐一切可能性,而非在短短几十年生命里只能实现极少数的可能性。
有关社会心理学能否以游戏中的虚拟实验补充乃至代替临场实验的问题,我不是专家,不好随意置评。我只想追问,这种做法在直观上为什么会让人有些犹豫。这其中涉及的是一个也许可以推而广之的问题:我们在玩游戏的时候,是否在物理身体之外也获得了一个虚拟的“身体”?毕竟,心理学研究的是一个与身体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心灵”(psyche),而非一个彻底抽离于身体的“心智”(mind);正是这一点要求被试的亲身在场(否则研究的结论将仅适用于人们在虚拟世界中的社会行为),也正是这一点导向了那些有争议乃至本质邪恶的实验(如著名的斯坦福监狱实验)。
电子计算机的模型刚刚提出的时候,先驱人物之一的阿兰·图灵(Alain Turing)就设想计算机模拟(simulation)能够将人的身体与心智相互分离;计算机模拟的本质是仅仅模仿心智的活动,将这种活动移植到一台依靠符号(0和1)来运作的机器之中。假如这个设想完全实现了,那么我们在电子游戏的世界里应当如同一团无形的“气”;我们应当仅仅作为各自的心智而彼此交流。我们今天对游戏的观念,很大程度上是基于图灵模型的:我们相信自己在游戏世界里感受不到疼痛,我们看着种种在现实世界中骇人听闻的暴力事件发生在游戏中,而完全不觉得有何不妥。但有另一种观点认为,所谓“心智”,一定是具身(embodied)的;它未必基于感官、疼痛,而只是说,即便我们在一个虚拟世界中活动,我们在一个特定时刻也只能占据一个特定的位置;我们不仅能够活动(action),而且能够受动(passion),即能够成为他人活动或非人事件的对象——凡此种种都揭示了我们在虚拟世界中的体验同样搭载在一个“身体”上。这也许是在虚拟世界中展开的种种研究的“元问题”,在此我不打算也不可能给出明确的答案,仅仅是给大家一个思考的契机。(J:这一段很有《知觉现象学》的味道呀。)
最后,我来讲一个影视作品中的相关案例。在电视剧《黑镜》(Black Mirror)第五季第一集(“Striking Vipers”)中,两个在现实世界中是好友的男性,因为偶然一起玩一个高度拟真的VR格斗游戏,作为游戏中的一男一女两个(有日本漫画感的)人物发展出了一段欲罢不能的肉体关系,令现实中的(J:各有伴侣、且为异性恋的)这两人尴尬无比。在当前的技术条件下,这还只是个虚构故事,是一个寓言;但我们已能真切地感受到,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由此追问:身体的界限究竟在哪里?
© 本文版权归 HomePhilosophy 所有,任何形式转载请联系作者。
© 了解版权计划
-
Miss Shao 赞了这篇日记 2021-03-12 23:3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