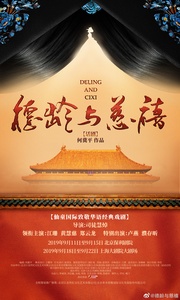关于《北京山本照相馆》
慈禧与德龄与她的照片
最近如果提及慈禧,舞台剧《德龄与慈禧》的复排让许多粉丝激动了一把,老戏骨+新生代的卡司搭配精致的服化道,让这部经典作品好评如潮,江珊的慈禧、郑云龙的光绪帝、郎玲的德龄无一不受到了好评,尤其是江珊老师的慈禧太后,从台词功底到情绪把控都让人佩服。

其实国内外的影视作品中也不乏聚焦于晚清题材,慈禧太后作为一个极具争议的角色也被众多不同的演员演绎过,但如果要说深入人心的慈禧形象却屈指可数。《走向共和》里吕中老师和《苍穹之昴》里的田中裕子老师堪称一时瑜亮。而卢燕老师在《末代皇帝》里,虽然只有短短几分钟的惊鸿一瞥,也是让人“过目难忘”,在《德龄与慈禧》最初的版本中,慈禧一角也是卢老师扮演,算是弥补了许多人当初没看过瘾的遗憾。



这几位对于慈禧,这个中国近代史上占据权力巅峰却又带来沉重灾难的女性的刻画地入木三分:傲慢、敏感、不安又有些歇斯底里,让张“反派”脸多了许多立体的视角,进而也让人物立体饱满了起来。再也不似史书中冰冷的评价,也不像那张著名的标准照——仪态端庄,但表情似乎显示出了一幅呆滞和苍白,可能是对舶来的新兴摄影术的一丝恐惧,又或者是身居高位的孤傲。从照片里能读出很多,但归根到底也只能算是后人的臆断。

关于慈禧的这张标准照、关于德龄与她之间的趣闻轶事,早已经成为了大众茶余饭后的闲聊话题,但至于这张照片的来源以及德龄与这张照片之间的关系,时至今日也还是鲜有人知晓。也算是碰巧,经过一系列艰难又不算特别艰难的工作后,《北京山本照像馆》这本书的中译版终于在上个月面市了。其中便花了三节的篇幅论述了本书主人公山本赞七郎与慈禧肖像照的渊源,以及德龄与慈禧之间的有趣互动。
作者在其中也引用了德龄自传《清宫二年记》的片段,她生动描述了哥哥勋龄使用摄影器材为慈禧太后拍摄、冲洗的过程。
当然《北京山本照像馆》作者日向康三郎先生的观点则是:为慈禧拍摄肖像照的摄影师是本书的主人公——日籍摄影师山本讃七郎,而非勋龄。暂且不论两者观点的真实与否,就单看慈禧太后拍摄照片这件事情本身,其实更具有一种感官上的冲击感。摄影术对于20世纪初的中国人而言,绝对算得上是高精尖的技术,1871年才刚刚研发出来的“干版摄影”技术到1900年也才只有30年不到的历史。如此高科技在当时人的眼中,并不亚于现在的“区块链”或者“人工智能”,而当这样一个代表着西方先进技术、代表着未来科技发展的“劳什子”遇上了代表着中国千年帝制最高者的慈禧太后,东方与西方、古老与先进、过去与未来、保守与革新……交汇在了这一张小小的照片上,无论它出自德龄兄长勋龄之手还是日本摄影师讃七郎的手笔,属于那个时代的图像记忆就这样封存下来了——当然也为后世的表演艺术家们重新演绎这段历史提供了许多参考。
撇开这张极具话题性的照片,本书的主人公作为一个日本人、也作为一个摄影师,亲身经历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东亚巨变,他个人命运也与中日两国的历史紧紧纠缠在了一起,从东京到北京他的人生经历不可谓不丰富,也藉此机会结识了中日两国诸多重要的达官显贵。另外作为那个时代鲜有可以掌控光影图像的人,在辽阔的中国北方讃七郎留下了足迹,用镜头记录下了属于那个时代的画面:建筑、人物、石窟、风景、肖像……客观上而言这些画面都属于那个时代中国记忆的一部分。
关于翻译
话题回到这本书的翻译工作,我也是第一次参与翻译正式出版的图书,诚惶诚恐地交稿、对稿、改稿,多次反复之后,越发觉得这样一份工作实属艰辛不易。不过相较于文学作品和学术作品,个人传记相对而言要毋庸置疑要简单很多。关于书的内容这里先不多做分享,以后再另写一文评论吧(挖个坑,填不填得上再说……)。这里先聊一些和这次翻译工作相关的日常吧。
东京的山本写真场
明治十五年(1882年)二十八岁的讃七郎在当时的东京府东京市芝区日影町一丁目一号开设了山本写真场,也就是现在位于东京市港区的新桥站东侧的站前广场。

2020年初,那时候国内新冠疫情刚刚从武汉爆发,全球已经开始陷入紧张,武汉封城更是让每个人都绷紧神经。我和顾老师却在那个时候“顶风作案”去了东京,因为是早先就定好的行程,一年工作出游一次机会实在不易,当然也是因为退改签损失有点大(这不还是因为贫穷),所以也就硬着头皮全副武装上了飞机。那时候疫情主要集中在湖北省,全国只有零星病例,而日本那边记得除了东京有3个案例,主要目光都集中在了漂泊在横滨港外的邮轮“钻石公主号”上。所以整体行程相对而言还没有那么艰难,只是全程的口罩,和新闻中滚动播放的信息,让人倍感不安。
成长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的我们这代人大多都有各种日剧情节,尤其是围绕着东京塔的故事,总让人感到温馨浪漫,我和顾老师也是如此,所以那次行程我有一个TODOlist就是开窗就能看到东京塔,同时兼顾每日出行的交通方便,我把Google Map打开研究了一下,居然发现了一个完美的地方——位于新桥站和汐留附近一家酒店。当然照相馆是不可能有的,可亲切感却是很也实在。

这时候东京的防疫措施基本没有,但好在日本人本身就有戴口罩的习惯,那个时候还觉得这种习惯和“全民洁癖”的性格应该能让日本成为疫情防控的一个标准范本(但后来的现实却把脸打得生疼,东京奥运这个“倒霉”的项目现在的情况已经很好地说明了一切)。在官方还没有启动全国措施的2月,东京地方的自治也已经看出普通公民已经对这次疫情有了一定的重视。在一家由四位老太太合作经营的一家小餐厅里(也是一家摄影主题的餐厅,一长整排的书架上从上到下摆满了各类摄影书籍),我们看到了和疫情相关的讲座活动预告,告诉大家一些相关常识,这让人有些佩服,也更加隐隐担忧国内的疫情状况。
彼时的中国新冠病例正处于爆发的增长期,而日本则在努力防范境外输入的阶段;待及此时截然相反的境遇,不得不说令人唏嘘。

这一切经历让人的思绪回到了这本书上,正如吕老师在译后记里所写的,我突然能够体会到讃七郎长女泷在差不多百年前肆虐的“西班牙大流感”中感染病故的那种无助感和悲伤,生命有时候很坚强,但有时候又格外的脆弱。
北京的山本照像馆
2020年8月,因为工作原因,又有机会来到北京出差,那时候的全国疫情已经趋于稳定,通过正常的防疫措施,一切出行活动都很顺利。而那次又很凑巧,住宿的地点又是在北京山本照像馆的不远处——灯市口。在白天工作之余,我便在晚上找了一辆共享单车,按图索骥,分别找到了位于霞公府街和王府井大街东二十六号的照相馆两个旧址。虽然照相馆早已经不复存在了:霞公府路南,现在是全部都是豪华的北京饭店,而王府井大街二十六号也应变为了私人住宅,闲人莫入。但因为翻译的缘故,却有了一种“故地重游”的小兴奋。


百年转眼过去了,北京和东京两座城市连同着背后的中日两个国家都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时过境迁、物是人非,未来会怎么样?后人最清楚了。
先写到这吧,挖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