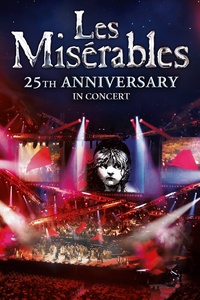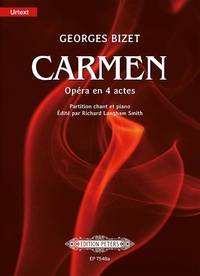我不知道我是不是正走在通往一无所有的道路上,我只知道拉上床帘,我就可以哭了。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
——T.S.Eliot
Ah,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yet may spend,
Before we too into the Dust descend;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Sans Wine, sans Song, sans Singer, and —— sans End!
——Omar Khayyam/Edward FitzGerald
每个心肠不会软化的人,其脑袋终必难逃软化的厄运。
——G.K.Chesterton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William Wordsworth
第一,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一一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人联为一体。……
第二,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因为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祟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第三,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
第四,保守主义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经济上的均等化并非经济进步。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
第五,保守主义相信旧习惯,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
第六,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改革并不是一回事,通常,创新更像是吞噬人类的火灾,而非进步的火炬。社会必须有所更张,因为缓慢的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就像人的身体永远都在自我更新一样。不过,上帝的护理是促成变化的恰当手段,检验政治家的标准是他是否体认到上帝护理之下的真正社会发展趋势。
——Russell Kirk
我听很老的老人说:
“万物都变易,
我们也一个个凋落。”
他们手如爪,腿膝
虬曲似老荆棘树枝,
傍着这流水。
我听很老的老人语:
“美好的一切终逝去,
就像这流水。”
——W.B.Yeats
突然之间,我回忆起来了。味道正是那块小玛德莱娜的味道,在孔布雷,每星期天早晨(因为星期天在做弥撒的钟响以前我不出门),我去莱奥妮姑妈的卧房请安,她总把小块蛋糕放进茶或椵茶里浸一下给我吃。可这天,我看到小玛德莱娜蛋糕,在品尝之前,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也许因为打那之后经常瞥见糕点店的货架上摆着小玛德莱娜,又没有再吃过,其形象早已和在孔布雷的那些日子分离,而和一些较近的日子联系上了;也许因为事隔已久,早被抛到记忆以外,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一切都已解体。形状——包括托着糕点的小贝壳形的衬纸,严肃而虔诚的打褶是那么富有肉感——消失了,或冬眠了,丧失了打入人们意识的扩张力。但是人在物丧,昔日的一切荡然无存,唯有气味和滋味还长久留存,尽管更微弱,却更富有生命力,更无形,更坚韧,更忠诚,有如灵魂,在万物的废墟上,让人们去回想,去等待,去盼望,在几乎摸不着的网点上不屈不挠地建起宏伟的回忆大厦。
一旦辨认出莱奥妮姑妈给我吃的那种用椵花茶浸过的小块蛋糕的味道(尽管我还不明白或要等到晚些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回忆使我那么高兴),在我眼前立即像戏台布景似的浮现临街的那座灰色老房子,姑妈的房间靠街面,另一面连接面朝花园的楼房,这是我父母在尾后加建的(这段截接的墙面迄今为止只有我重见过),随即浮现城市,从早到晚的城市,时时刻刻的城市,浮现我午饭前常去的广场,浮现我常去买东西的街道,浮现我们天晴时常去的道路。如同日本人玩的那种游戏:他们把原先难以区分的小纸片浸入盛满水的瓷碗里,纸片刚一入水便舒展开来,显其轮廓,露其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变成花朵,有的变成房屋,有的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同样,我们花园的各色花朵,斯万先生大花园的花朵,维沃纳河畔的睡莲,村子里善良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小房子和教堂乃至整个孔布雷及其周围,不管是城池还是花园,统统有形有貌地从我的茶杯里喷薄而出。
——M.Prust
文学上的古典主义者,政治上的保皇派,宗教上的英国国教高教会派。
——T.S.Eliot
Ah, make the most of what we yet may spend,
Before we too into the Dust descend;
Dust into Dust, and under Dust to lie,
Sans Wine, sans Song, sans Singer, and —— sans End!
——Omar Khayyam/Edward FitzGerald
每个心肠不会软化的人,其脑袋终必难逃软化的厄运。
——G.K.Chesterton
The Child is father of the Man;
And I could wish my days to be
Bound each to each by natural piety.
——William Wordsworth
第一,保守主义确信存在着某种主导社会生活和个人良心的神圣意志一一它在权利和义务之间建立起永恒的联系,将伟人和凡人、活人与死人联为一体。……
第二,保守主义珍爱多姿多彩并带有神秘性的传统生活,因为它明显区别于大多数激进观念体系所推祟的日益狭隘的整齐划一,以及平等主义和功利主义的目标。……
第三,保守主义坚信文明社会需要多种秩序和等级。……
第四,保守主义相信财产和自由密不可分,经济上的均等化并非经济进步。如果消灭私人财产,自由将不复存在。
第五,保守主义相信旧习惯,不信任“诡辩家和算计者”。……
第六,保守主义认为变化与改革并不是一回事,通常,创新更像是吞噬人类的火灾,而非进步的火炬。社会必须有所更张,因为缓慢的变化是自我保存的途径,就像人的身体永远都在自我更新一样。不过,上帝的护理是促成变化的恰当手段,检验政治家的标准是他是否体认到上帝护理之下的真正社会发展趋势。
——Russell Kirk
我听很老的老人说:
“万物都变易,
我们也一个个凋落。”
他们手如爪,腿膝
虬曲似老荆棘树枝,
傍着这流水。
我听很老的老人语:
“美好的一切终逝去,
就像这流水。”
——W.B.Yeats
突然之间,我回忆起来了。味道正是那块小玛德莱娜的味道,在孔布雷,每星期天早晨(因为星期天在做弥撒的钟响以前我不出门),我去莱奥妮姑妈的卧房请安,她总把小块蛋糕放进茶或椵茶里浸一下给我吃。可这天,我看到小玛德莱娜蛋糕,在品尝之前,什么也没有想起来;也许因为打那之后经常瞥见糕点店的货架上摆着小玛德莱娜,又没有再吃过,其形象早已和在孔布雷的那些日子分离,而和一些较近的日子联系上了;也许因为事隔已久,早被抛到记忆以外,什么也没有残留下来,一切都已解体。形状——包括托着糕点的小贝壳形的衬纸,严肃而虔诚的打褶是那么富有肉感——消失了,或冬眠了,丧失了打入人们意识的扩张力。但是人在物丧,昔日的一切荡然无存,唯有气味和滋味还长久留存,尽管更微弱,却更富有生命力,更无形,更坚韧,更忠诚,有如灵魂,在万物的废墟上,让人们去回想,去等待,去盼望,在几乎摸不着的网点上不屈不挠地建起宏伟的回忆大厦。
一旦辨认出莱奥妮姑妈给我吃的那种用椵花茶浸过的小块蛋糕的味道(尽管我还不明白或要等到晚些时候才明白为什么这个回忆使我那么高兴),在我眼前立即像戏台布景似的浮现临街的那座灰色老房子,姑妈的房间靠街面,另一面连接面朝花园的楼房,这是我父母在尾后加建的(这段截接的墙面迄今为止只有我重见过),随即浮现城市,从早到晚的城市,时时刻刻的城市,浮现我午饭前常去的广场,浮现我常去买东西的街道,浮现我们天晴时常去的道路。如同日本人玩的那种游戏:他们把原先难以区分的小纸片浸入盛满水的瓷碗里,纸片刚一入水便舒展开来,显其轮廓,露其颜色,各不相同,有的变成花朵,有的变成房屋,有的变成活灵活现的人物。同样,我们花园的各色花朵,斯万先生大花园的花朵,维沃纳河畔的睡莲,村子里善良的居民连同他们的小房子和教堂乃至整个孔布雷及其周围,不管是城池还是花园,统统有形有貌地从我的茶杯里喷薄而出。
——M.Prust
订阅Jussariah的收藏:
feed: rss 2.0